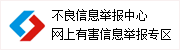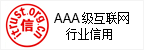鲁崇民:史笔与诗心的交融——杨焕亭《半纪耕耘逐时新》评论特质
在作家梦萌文学创作五十周年之际,相关评论佳作迭出,其中作家、评论家杨焕亭的《半纪耕耘逐时新》尤为引人注目。这篇文字不仅是对梦萌半世纪文学实践的全景扫描,更以其独特笔法成为当代作家评论的典范——它以“史笔”的严谨梳理创作脉络,以“诗心”的温度照见文学本质,在“梳理”与“阐释”“实证”与“感悟”之间找到精妙平衡,既勾勒出梦萌“坚守与求新”的精神图谱,更彰显出“史论结合、情理交融”的鲜明特质。其评论特质可概括为四方面:
一、以“史”为经:脉络梳理的严谨性与创作内核的精准锚定
杨焕亭的评论首先体现出清晰的历史意识。多年来,他一直是梦萌创作实践的追踪者,这为他解读梦萌作品提供时空的条件。故而他以时间为轴,将梦萌的创作划分为“早期作品《爱河》”“九十年代《悲喜娱乐城》”“关注城乡二元的《倾城》《金喽啰》”“反思人类生存的《新部落》”等阶段,既呈现了作家题材选择从“水文化”到“生态危机”的拓展,也揭示了其批判视野从“社会现象”到“人类命运”的深化。这种梳理绝非简单的作品罗列,而是紧扣“半纪耕耘逐时新”的核心命题——每个阶段的分析都指向“新”的内涵:《爱河》对“水文化”的发掘是题材新探索,《悲喜娱乐城》的文化批判是思想新维度,《倾城》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关注是视野新拓展,《金喽啰》作为《倾城》批判精神的延续,通过传销群体的命运进一步剖析金钱对人性的异化,展现乡村文化基因在城市中被金钱扭曲的利益观裹挟下的碰撞与异化,《新部落》对人类生存的反思则是格局新提升。
对散文与诗歌的纳入更显整体性。杨焕亭不仅聚焦长篇小说,更将散文的“生命意识”“内省意识”与诗歌的“风格统一”纳入论述,完整勾勒出梦萌“小说、散文、诗歌相映生辉”的创作体系。其中,诗歌虽未详述具体内容,但明确其与其他文体在“时代印记”与“抒情底色”上的统一性,这种全景式观照避免了评论常见的“以偏概全”,让“半纪耕耘”的厚度得以充分彰显。
尤为关键的是,杨焕亭精准抓住了梦萌创作的核心特质——“对时代主题的全息跟进”与“文学本质的执着守护”的辩证统一。他指出,梦萌的“逐时新”绝非被动描摹,而是带着主动思考与批判:《悲喜娱乐城》中“鬼城”作为市场经济初期畸形文化的“怪胎”,承载着市民从渴望到幻灭的集体记忆;《倾城》通过全皓、麦娜等青年的漂泊命运,直击城乡二元结构的痛点,揭示“改制”被权力扭曲后底层人的生存困境;《新部落》更超越社会现象,以豪哥等人的“巢居”“穴居”经历,完成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这种对创作内核的精准把握,让“史”的梳理始终围绕“精神图谱”展开,避免了流于表面的编年式罗列。
二、以“论”为纬:文本阐释的穿透力与理论工具的恰切运用
评论的深度,在于对作品肌理的精准剖析。杨焕亭擅长从具体文本中提炼精神内核:分析《悲喜娱乐城》时,他抓住“鬼城”这一象征体,揭示其作为“畸形经济文化怪胎”的隐喻意义,铺陈市民与文化人的命运沉浮;解读《新部落》时,通过“巢居”“穴居”的超现实设定,引申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呼应恩格斯“自然界的报复”的警示;探讨《倾城》的“帆布厂”意象,则将其与城乡变迁中个体的漂泊绑定,让符号承载起时代的重量。这种阐释不是脱离文本的空泛议论,而是“从作品中来,到思想中去”,既有文本依据,又有哲学提升。
在叙事艺术层面,杨焕亭的分析展现了对文学本体的深刻理解。他指出梦萌“严格遵循艺术的‘自律性’”,这种“自律”体现在对传统叙事精髓的坚守:《爱河》的传奇性、《新部落》的悬念营造,延续了中国小说“铺排故事、营造气氛”的传统,让作品始终保持着“欲罢不能”的阅读张力。而“动物伦理的落差”“人的‘兽化’与兽的‘人化’”等笔法(如《新部落》中猴子与小狗的“人性”视角),则显示出对现代叙事技巧的吸纳,体现了对当代文学理论成果的主动借鉴——通过打破人与动物的界限,既强化了生态主题的表达,也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审美视角。
理论工具的运用尤为恰当。他引用刘建军对“水文化”的论断解读《爱河》,借黑格尔“象征是艺术的开始”阐释梦萌的意象运用(如“鬼城”“帆布厂”“棺材”等象征体,表现出梦萌前卫的文学思维),用马克思“人就是人的最高本质”呼应散文中对“人的本质力量和价值的美学肯定”(如《多梦人生》将渭水化为“书简”“宝剑”,正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具象化赞美),甚至将荀子与海德格尔的思想融入对“内省意识”的分析(如散文中对“舌头功能”的讽喻、对“猴性”的探问,既延续了中国文人“修身”传统,也呼应了现代性对“人如何自处”的追问)。这些理论并非炫技式的堆砌,而是与作品特质形成“对话”,让评论既有学术分量,又不晦涩难懂。
三、以“情”为魂:评论语境的温度感与“理解之同情”
不同于纯学术评论的冰冷,杨焕亭的文字始终带着温润的情感。开篇“但见时光流似箭”的引语,既点出半个世纪的创作跨度,又暗含对岁月沉淀的感慨;结尾“健笔纵横,健步奔向茶寿”的祝愿,字里行间是对前辈作家的敬意。分析作品时,他用“温暖而又苍凉的悲悯精神”(评《倾城》)、“蓬勃的诗意存在”(评整体创作)等饱含情感的表述,传递出对作品艺术魅力的真切感知。
这种温度更体现在“理解之同情”的态度中。杨焕亭既肯定梦萌“全息跟进时代”的敏锐,也理解其“浪漫与现实主义结合”的创作选择:这种结合既体现在内容层面的现实描摹与浪漫批判(《悲喜娱乐城》中市民对“鬼城”的狂热议论是现实主义的“在场”,而“鬼城”的寓言式荒诞感又充满浪漫主义的批判张力;《新部落》里豪哥开发引发的生存危机是对现实的警示,而猴子、小狗的“人性”视角与“巢居”“穴居”的超现实设定,则让生态批判获得更灵动的表达),也通过语言的“时代感”(现实)与“诗意感”(浪漫)得以具象化。他既赞赏其“文化批判的勇气”(如《悲喜娱乐城》不回避畸形文化的尖锐,《倾城》直面改革中的权力扭曲),也尊重其“风格统一”的艺术追求,尤其对一位老作家而言,这种在坚守中求新的创作选择更显珍贵(如诗歌与小说、散文在“时代印记”与“抒情底色”上的呼应)。这种评论姿态,超越了“褒贬”的简单维度,成为与作家、作品的平等对话——正如他笔下梦萌的文学世界充满“对人的尊严的守望”,他的评论也充满对文学本身的敬畏。
四、以“文”为桥:语言表达的文学性与文化底蕴的融合
优秀的评论,本身也是一篇好文章。杨焕亭的语言兼具学术的精准与散文的灵动:论述理论时,他用“全息跟进”“艺术自律性”等术语保证严谨;描绘作品时,又以“波谲云诡,悬念迭出”(评叙事风格)、“字里行间闪烁着老子的生命哲学”(评散文意境,既延续了孔子“逝者如斯夫”、蒋捷《虞美人·听雨》的传统生命咏叹,又融入老子“归根曰静”的哲学思考,更从夏的“绿帜妊娠”、秋的“失墒龟裂”中提炼生命律动,让传统哲思与自然意象形成互文)等表达传递美感。这种语言风格与梦萌“诗意感”“幽默感”的创作特质形成奇妙的呼应——如对传销者的戏谑刻画(《金喽啰》)、对“舌头功能”的辛辣讽喻(散文),既显语言的幽默感,又能让读者在笑中领悟真谛——让评论与评论对象在文体上达成和谐。
引用的恰到好处更添文采。从恩格斯“自然界的报复”(呼应《新部落》的生态思考)到欧阳修“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对照《多梦人生》中渭水意象的文化情怀),从孔子“逝者如斯夫”到蒋捷《虞美人·听雨》(映衬散文中的生命意识),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名言警句自然融入行文,既丰富了表达,又提升了文化品位。
综上,杨焕亭的《半纪耕耘逐时新》的评论特质,正是“史笔”与“诗心”的完美交融:以史笔立骨,确保论述的严谨与深刻;以诗心为魂,赋予文字温度与灵动。它不仅为我们解读梦萌的“坚守与求新”提供了范本,更昭示了文学评论应有的姿态——在理性与感性的平衡中,完成对文学本质的守望。
责任编辑:李欢颜
2025-08-05 11:29:28
2025-08-05 09:04:49
2025-08-05 09:02:44
2025-08-05 09:00:49
2025-08-05 08:58:52
2025-08-04 11:45:55
2025-08-03 10:42:14
新闻动态
公益明星
榜样人物
草根故事
热门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