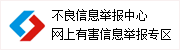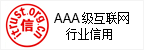张鹏:小议梦萌的长篇小说《悲喜娱乐城》
一、时代现场的精准捕捉:
《悲喜娱乐城》的叙事根基深植于20世纪90年代的特殊历史语境。市场经济浪潮奔涌,计划经济的惯性尚未完全消退,商业社会的“利润最大化”,初入市场的权力寻租,繁华喧嚣下的“精神空虚”,构成了斑斓耀熠的时代舞台。把“鬼城”的兴建、繁盛与毁灭置于宏观社会转型中,完成对时代症候的精准切片:
“鬼城官司”的核心矛盾,并非简单的经济纠纷,而是权力与资本的深度勾连。连向北(前任市委书记的兄弟、现任中院院长的叔叔)、丁干然(现任市委书记的外甥、经济庭庭长兼法院院长)等人物,将法律异化为权力寻租的工具:连向北通过“预设财产阴谋”转移资产,丁干然利用职权操控案件走向,甚至将“鬼城官司”变为“官场权力斗争的重大筹码”。当法庭的庄严成为利益的秀场,普通集资户的维权之路注定艰难。而这场官司的起因和结束,不过是新旧权力交替下,一个看似荒诞的女性的复仇所引起的。
“鬼城”作为市民集资兴建的娱乐项目,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设施,亦不是纯粹的商业娱乐场所,而是被“发财焦虑”与“投机心理”驱动的政商结合的“文化怪胎”——对于“鬼”的刺激的追求,掩盖了文化内核的缺失;主体之诡谲也是权力寻租的初夜。开业时万人空巷,倒闭时债务缠身。这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轨迹,恰是90年代“开发区热”“集资热”的缩影。正如邢建海在评论中所言:“‘鬼城’是尚未扩散的‘癌细胞’,是社会肌体上的‘肿瘤’。”它的存在与崩塌,直接指向转型期经济秩序的混乱与投机文化的泛滥。
主人公殷小铨的形象,是转型期文化人的典型缩影。他自称“膨胀诗人”“天才雄辩家”,却因市场经济浪潮沦为“失败的弄潮儿”:卖过书稿、蹬过三轮、开过摩的,为二百多名集资户打四五年官司,挨过毒打、遭过车祸,却始终“没有低下尊贵的头颅”。他的矛盾性在于:既是“物质的乞丐”(为生计奔波),又是“精神的贵族”(坚守文人尊严);既沉迷于情场的放纵(与晶晶、雪儿等女性的纠葛),又在法庭上以雄辩才华对抗权力。殷小铨在法庭上的雄辩“喷礴如潮”,连资深律师都“俯首称臣”;但面对集资户的苦难,他又因“无权无势”屡遭挫败——这种“能力与处境的错位”,正是时代对个体的挤压。这种矛盾与割裂,是90年代文化人“理想主义”与“生存焦虑”双重困境的真实写照。
二、人性光谱的多维呈现:
梦萌对人性的勘探,深入到欲望、道德、生存本能的交织地带,通过多组人物的命运对照,呈现出人性的复杂光谱。
殷小铨的生命轨迹,是一场“狂欢—幻灭—重生”的精神史诗。作为“膨胀诗人”,他将生命能量挥霍于情欲与权力的角力中。与晶晶的恋爱是纯情的萌芽,与雪儿的同居是生存的依赖,与市委书记夫人的幽会是权力的试探,每一次情感纠葛都裹挟着对“被认可”的渴望。他在法庭上的雄辩、在酒桌上的机锋、在女人面前的“万能”,本质上是被压抑的“自我”对“被看见”的疯狂追逐。
当“鬼城”崩塌、官司败诉、亲友离散,他终于意识到“膨胀”的虚妄:金钱买不来尊严,权力护不住真心,情欲填不满空虚。独臂哑巴的纵火、晶晶的背叛、费希蒙的坚守,成为他“觉醒”的催化剂。鬼城大火中,他从复仇的癫狂转入对生命的悲悯。精神张扬和生命张力的个体追寻与担荷苦难悲悯大众的文人风骨,在这一刻合而为一,他在大火中涅槃重生。正如王仲生所言:“他的牺牲不是道德的完胜,而是生命的觉醒——在毁灭中,他终于找到了比‘自我’更重要的东西。”
费希蒙作为殷小铨的对照,是“清醒的理想主义者”。他始终保持着文人的清高与底线:拒绝与权力同流合污,坚持为集资户发声,最终抚养殷小铨的遗孤。他的存在,象征着知识分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当殷小铨在大火中完成“自我救赎”,费希蒙在法庭外为遗孤奔走,则完成了“精神传承”的隐喻——个体的牺牲或许微不足道,但人文精神的火种终将延续。
独臂哑巴是小说中最具悲剧性的“他者”。作为连向北与金银花的私生子,他是社会转型期原罪的直接见证者:目睹父亲的权谋、母亲的堕落、姐姐晶晶的背叛,却因生理残缺与社会排斥,始终处于“被遗忘的角落”。他的复仇是连向北(权力)、晶晶(欲望)以及“许多钱和纸条”(金钱),他从本能的朴质的判断中选择了背离亲情人伦,出卖身体,攫取利益的一方作为复仇对象,是对社会转型期原罪的复仇。他的沉默与阴鸷,是长期被压迫的生存本能;他的纵火,既是对父辈罪孽的复仇,亦是对社会污浊的净化。他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这种矛盾性,揭示了转型期个体的异化。这一形象,又契合于《庄子》中“畸人”的论述,是转型其社会原罪的裁判。
三、人文精神的理想投射:法律、道德与秩序的重建
《悲喜娱乐城》的深刻性,不仅在于对时代病症的揭露,更在于对“如何疗愈”的思考。小说通过“鬼城官司”的荒诞结局与人物命运的转折,传递出对法治重建、道德回归与秩序重构的迫切期待。
小说中,法律的“工具化”是最尖锐的批判。丁干然作为法官,利用职权操控案件走向;连向北作为“司法界的关系户”,将法庭变为权力秀场。这种“人治”对“法治”的侵蚀,让集资户的维权之路沦为“闹剧”。但小说并未止步于批判:殷小铨与费希蒙始终坚持“用法律维权”,哪怕屡遭挫败;独臂哑巴的纵火,本质上是对“非法秩序”的暴力反抗;最终,费希蒙通过法律程序为殷小铨争取到“烈士”称号,虽迟到却仍具意义。这种“批判中的坚守”,传递出对“法治中国”的信念——法律或许会被权力污染,但对正义的追求永不熄灭。
道德崩塌是转型期的另一重危机。连向北夫妇因贪婪走向毁灭,晶晶面对权力与金钱的堕落,丁干然“爱情”掩盖下的贪婪,这些角色的悲剧,本质上是“道德失序”的恶果。但小说中仍有微光:费希蒙对遗孤的抚养、殷小铨舍身救人的选择、独臂哑巴临终前的忏悔,都在证明“人性本善”的底色从未消失。
小说结尾,费希蒙对养子(殷小铨遗孤)说:“明天是你们的,就由你们安排吧!但要答应我,上街要遵守交通秩序,去公园要遵守游戏规则。”这句看似寻常的叮嘱,实则是对“新秩序”的深情呼唤。它既包含对法治的期待(“遵守交通秩序”),也指向对规则的敬畏(“遵守游戏规则”),更隐含着对“下一代”的信任——当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如连向北、丁干然)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或将以更理性的姿态重建社会。
四、《悲喜娱乐城》的艺术成就,不仅在于内容的深刻,更在于形式的创新。梦萌以“单元式结构”与“象征系统”的互文,完成了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突破。
小说采用单元式叙事,将“鬼城兴建”“集资狂热”“官司拉锯”“纵火焚城”“精神救赎”等关键事件切割为独立单元,又以“鬼城”为线索串联。这种“跳跃式”结构,看似割裂,实则与90年代社会的“浮躁”形成同构:时代的巨变如同湍急的河流,个体的命运如同一叶扁舟,被时代的浪潮推着向前,来不及细细品味悲喜。单元间的留白与跳跃,与所表现的时代的巨变与浮躁形成一种对应。
“鬼城”是小说的核心象征体,其意蕴随叙事推进不断深化:在故事的开始,它是泡沫经济的“文化怪胎”,象征投机狂热的荒诞性;随着连向北走向前台,它是权力寻租的“交易场”,象征权力寻租的腐败性;“鬼城”借助晶晶变成“夏威夷夜总会”,它又是人性的“照妖镜”,照见欲望的膨胀与道德的崩塌;最后,它的焚毁与重生,象征旧秩序的瓦解与新精神的觉醒。
梦萌的语言风格呈现“杂糅”特征:文人对话的机锋(如殷小铨与费希蒙的诗词唱和)、市井俚语的粗鄙(如集资户的争吵)、官场套话的虚伪(如连向北的“原则性发言”),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风格断裂”,恰恰是转型期社会“阶层分化”的真实映射——不同群体说着不同的语言,遵循不同的逻辑,却共同构成时代的复杂图景。
《悲喜娱乐城》是一部“时代的寓言”,更是一曲“灵魂的史诗”。梦萌以犀利的笔触解剖了90年代的社会病灶,又以悲悯的情怀凝视人性的复杂;他既揭露了权力与资本对个体的碾压,又坚信人文精神的火种终将延续。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它的主题和艺术仍然有夺目的光芒。真正的“鬼城”,从来不是物质的废墟,而是精神的荒原;真正的“重生”,从来不是简单的物质重建,而是灵魂的涅槃。
责任编辑:李欢颜
2025-08-05 09:04:49
2025-08-05 09:02:44
2025-08-05 09:00:49
2025-08-05 08:58:52
2025-08-04 11:45:55
2025-08-03 10:42:14
新闻动态
公益明星
榜样人物
草根故事
热门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