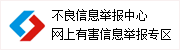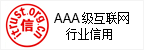岐山:悬着三千年的光
我的老家在扶风,八十年代前对邻县岐山的印象,仅停留在接壤的益店镇;后来参加工作,常与岐山人共事,尤其我的班长——一位地道岐山人,他在我成长路上的帮扶,至今仍清晰如昨。那时市级部门流传一句戏言:“扶风人是写‘同志们’的,岐山人是念‘同志们’的”,话里藏着对岐山“人杰地灵”的笃定——这里的文化人扎堆,知名作家、画家不在少数,单是岐山籍院士便有五六位。这份渊源与敬佩,让我始终想为岐山写点什么。
要写岐山,得先触到它的“根”。岐山县踞于陕西中部、关中平原西端,宝鸡市东北部,北接麟游,南连太白,东依我的老家扶风与眉县,西邻凤翔、陈仓,辖9镇,常住人口35.38万。它的名字是“老天刻下的”——六盘山东延支脉千山余脉在此驻足,主峰箭括岭双峰对峙、山分两岐,“岐山”之名便由此烙进史册,古称“西岐”。地貌呈“凹”字形:北枕岐山主脉,南抵秦岭余麓,中部是渭水冲积出的洪积扇平原、黄土台原与河谷阶地,渭水、韦河穿境而过,冲刷出北塬、七里塬、碛雍塬三塬并列的格局,恰是“两山夹一川,两水分三塬”的生动注脚。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型,四季界限分明:春回暖时仍裹寒潮,夏热雨来却不均,初秋阴雨锁层林,晚秋风爽天湛蓝,冬冷干燥少雪霜——这般山河与气候,早为它的“不凡”埋下伏笔。
“西岐”二字而非虚名,它藏着“华夏文明源头”的密码——隋开皇十六年始设县,2200余年建制史的背后,是更绵长的文明根系。这里是炎帝重要生息地,是农耕始祖后稷教民播谷的故土,一粒粒谷种在此破土,点燃华夏农耕的第一簇火种;是中医始祖岐伯悬壶济世之处,《黄帝内经》的思想萌芽,便从这片土地悄然抽枝。而最让它熠熠生辉的,是“周室肇基之地”的身份:周人迁此,文王被拘而演《周易》,智慧在困境中凝成六十四卦;武王伐纣定天下,开启赫赫宗周王朝;周公旦在凤凰山南麓制礼作乐,搭起“礼仪之邦”的框架,更成后世儒家思想的源头。这里是3000年前西周的都城,是《诗经》里“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的都邑,更是当时世界性的最大人口聚集地,堪称“西周时期的世界之都”。2004年周公庙遗址出土的2万多片刻辞甲骨中,4片清晰刻着“周公”字样;另有1.1万片西周甲骨修复后,可辨刻辞2600个——这些骨片上的纹路,都是三千年文明最直接的见证。
它还是“青铜器之乡”,出土的青铜器种类最齐、铭文最长——毛公鼎、伯克壶、王方鼎、牛尊等每一件捧出来,都是考古界举足轻重的珍品。就连三国诸葛丞相的故事,也与这里紧紧缠绕:五丈原是他星落之处,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凭吊,让“鞠躬尽瘁”的精神,成了岐山另一重深刻的文化印记。
岐山县的历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它是周文化的发祥地,藏着丰饶的历史遗迹与文化景观。最著名的当属周公庙,既是纪念周公旦的圣地,也是岐山县的标志性建筑。漫步庙内,仿佛脚踩时空缝隙,能触到古人的智慧与文化的温度。此外,五丈原风景名胜区内涵丰厚,人文景观荟萃,亦是不可错过的去处。
站在五丈原的晨光里,看渭水如碧带绕着平畴舒展,忽然就懂了“龙脉之地”的意涵——这方被秦岭与千山夹抱的川塬,南接渭水,北枕岐山,像一柄被岁月磨亮的玉圭,从炎帝生息的远古,一直悬到如今。风过处,既有周公庙古柏的苍响,也有臊子面出锅时的酸香,三千年光阴,竟都凝在这山河与烟火的褶皱里。
如今再登周公庙,唐代的侧柏仍举着1300多年的浓荫,汉代的国槐把虬枝探进《诗经·卷阿》里“飘风自南”的意境。庙内62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气势恢宏:周公殿、太公殿的飞檐挑着晨光,乐楼壁画上的周朝乐舞还凝着当年的韵律,玄武“玉石爷”的宝剑仍泛着唐时的冷光。最动人的是那些石碑,韩愈、苏轼的诗文刻在上面,连同殿内“以德治国”的展板,把周公“握发吐哺”的勤政、“德才兼备”的智慧,酿成了比古柏更绵长的气息。难怪这里成了多所院校的教学基地,往来者摸着展柜里的甲骨残片,就像摸着了周文化跳动的脉搏。
从周公庙穿过县城,便到了蔡家坡——这片曾在历史里留下兵戈印记的土地,如今已是岐山工业的“心脏”。再往东南行,便是五丈原。那方高五十余丈的土塬,状如琵琶,三面凌空,渭水在脚下绕成天然屏障,《地理通志》称它“高、平、旷、远,兵家必争之地”,可如今人们记着的,全是诸葛孔明的故事。唐初修建的武侯祠里,岳飞手书的《前后出师表》刻在40块青石上,笔力遒劲如铁,与诸葛亮的文辞并称“双绝”;献殿里的泥塑坐像,纶巾羽扇,脸色虽带几分病容,却仍透着运筹帷幄的气度。参观时导游会指着落星亭里的青褐奇石说:“那是孔明陨落时坠下的将星”;再指着衣冠冢讲:“他遗嘱薄葬,连陪葬品都没有”。站在塬上极目远眺,渭水、韦河如银线缠绕,平畴千里似锦绣铺展,忽然就想起温庭筠的诗:“下国卧龙空寐主,中原得鹿不由人”——可司马懿那句“天下奇才也”的叹服,还有这千年不荒的祠堂,早把“鞠躬尽瘁”四个字,刻成了比石碑更持久的印记。
若说周公庙藏着岐山的“骨”(文明之骨),那市井间的吃食便藏着它的“魂”(生活之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果你来到周礼之乡、凤鸣岐山,不能光看三千年膴膴周原的流光溢彩,更要品尝一口西岐大地的“神来之食”——岐山臊子面。
岐山臊子面,当地人叫“咥一碗”,语气里满是亲昵与自豪,这面真担得起“神来之食”的名号:它源于周代“馂馀之礼”,文王泼汤祭祖的习俗,演变成如今“第一碗敬天地”的规矩;食材要凑齐五色——红萝卜的红、黄花菜的黄、蒜苗的绿、木耳的黑、豆腐的白,像把《周易》的五行哲理揉进了碗里;做法更有讲究,汤要“煎、稀、汪”,面要“薄、筋、光”,味要“酸、辣、香”,灵魂则是岐山醋——经五谷熬煮二十多道工序,酸得醇厚不刺喉,恰似调和了人生五味。唐太宗曾为它驻足,慈禧曾御赐“天下第一面食”,可最动人的还是农家灶上的场景:主妇燷着臊子,醋香飘满整个院子,端碗时一手扶沿、一手执筷,七寸六分的筷子暗合“七情六欲”,夹起面条的瞬间,竟像是把《周易》的哲思、周礼的规矩,都一口吃进了心里。所以岐山臊子面的特点有九字谣高度概括——汤:煎、稀、汪;味:酸、辣、香;面:薄、筋、光。酸入肝、甜入脾、苦入心、辣入肺、咸入肾,与《黄帝内经》中的脏象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相关联。一碗岐山臊子面其中五形五色尽显、五味俱全、五脏得以涵养,六腑得以滋润,金、木、水、火、土五行中的相生相克尽在其中。
除了臊子面,岐山的吃食个个藏着巧思:擀面皮要切得细匀,浇上油泼辣子,酸香能勾人魂;醋粉用酿醋剩下的醋糟制成,软而不烂,自带发酵的清酸;油酥锅盔烤得外脆里嫩,配一碗清粥就能扛一上午的力气;西府合盘里的肘花、皮冻,浇上一勺岐山醋汁,便成了宴会上少不了的热闹滋味。这些吃食里,全是岐山人的生活智慧:把醋糟变废为宝成美食,把古老礼仪融入日常三餐,就像他们脚下的土地,既装得下西周的青铜鼎,也盛得下灶台上的粗陶瓦罐。
而这片土地的“力”,正藏在轰鸣的厂房与转动的齿轮里——岐山的工业脉络,本就与蔡家坡的成长紧密交织。作为西北地区老牌工业基地的核心,蔡家坡的工业基因早在上世纪便已铸就:抗日战争时期,陕棉九厂的纱锭昼夜转动,西北机器厂的零件、渭河工具厂的器械,为革命事业注入硬核力量;三线建设时期,这里更成了工业布局的关键节点。到了新时代,作为陕西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蔡家坡一一它已蜕变为西北工业重镇、宝鸡市副中心城市,常住人口超二十万,是陇海铁路西安与宝鸡之间一颗璀璨的“工业明珠”。如今,岐山县及蔡家坡,工业版图愈发清晰:陕汽、法士特、海螺水泥等207户“五上”企业扎根于此,2100多户中小微企业蓬勃生长,10万产业工人锻造着2200多个品种的重型车桥、变速箱等核心部件——2024年,蔡家坡整车销量达2.2万辆,汽车及零部件产值突破147亿元,就连九三阅兵方阵里的重卡,也印着“岐山制造”的深刻印记。从抗战起步到三线发展,再到如今以汽车产业为核心的集群效应,蔡家坡早已成为岐山县乃至宝鸡市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如果说“一座庙”载着文明根脉,“一碗面”裹着生活温度,那“一辆车”(及它背后的蔡家坡工业)便托着这座城的硬核底气——三者交织,成了岐山对外最亮的名片。
暮色降临时,再看岐山——箭括岭的轮廓渐渐浸在暮色里,周公庙的灯光次第亮起,街边面馆的蒸汽裹着浓郁的醋香飘过来,蔡家坡厂房的灯火与星子连成一片。忽然明白,这方土地之所以动人,从不是因为“西周世界之都”的过往,而是三千年的文明从未断层:周公的礼、孔明的忠,都化作了周公庙古柏的年轮;炎帝的耕、岐伯的医,都酿成了碗里臊子面的酸香;而蔡家坡工业的钢与火,正让古老的光在新时代愈发璀璨。当你端起一碗面,筷子挑起的不只是雪白的面条;当你望向蔡家坡的灯火,看到的不只是转动的齿轮——那都是从周原飘来的风,是悬在光阴里的光,从炎帝播下第一粒谷种时便已亮起,三千年过去,从来就没暗过。
作者简介:退休公务员,高级经济师
责任编辑:李欢颜
2025-10-10 17:29:54
2025-10-10 17:27:24
2025-09-30 15:51:35
2025-09-30 15:50:39
2025-09-30 11:59:59
2025-09-29 11:38:35
新闻动态
公益明星
榜样人物
草根故事
热门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