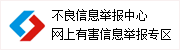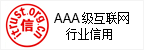岁月深处的夏秋童年
今年的太阳像被钉死在天上,从春到夏至秋没正经落过几场雨,热得人夜里翻来覆去,像烙饼似的。恍惚间,思绪总被风牵着飘回五十多年前的夏秋,那些被蝉鸣、蝌蚪、大枣、星光填满的日子,藏着太多能泡透时光的清凉。
外婆家后院的土夯城墙,是那段岁月最鲜明的坐标。修墙取土挖出的壕沟积了雨水,成了城壕——这壕沟南北窄、东西长,像条细长的带子。一米多深的水里,芦苇摇着绿影,野鱼在水草底吐泡泡,成群的“蛤蟆骨朵”,也就是小蝌蚪,挤作一团,尾巴一摇一晃划着水,把水面搅得微微发颤。青蛙游得欢实,后腿蹬得像装了小马达,时不时探出头“咯哇咯哇”叫,声音混着水纹荡开,引得蜻蜓低飞,翅膀扫过涟漪时,惊得小鱼窜出水面又“扑通”扎下去。
妇女们常聚在城壕边洗衣,棒槌“砰砰”砸着衣裳,笑声混在水汽里,把热天浸得软乎乎的。老表叫花哥是孩子王,脱了裤子“扑腾”一声扎进水里,溅起的水花漫过半人高。其他伙伴跟着“噗通噗通”往下跳,水里顿时炸开了锅:狗刨得溅起浑水,打水仗的扯着嗓子喊,闹得芦苇乱晃,惊飞了蜻蜓。洗衣的妇女们笑着骂“疯小子”,棒槌却没停,水珠滴进水里,和孩子们的浪混在一处。
我不会水,蹲在岸边专心捞蛤蟆骨朵:圆滚滚的小家伙黑得发亮,一触到指尖就往水草里钻,得耐着性子慢慢拢,才能捞几只放进玻璃瓶。要么就盯着水里的小鱼,看它们甩着尾巴从石缝里窜出来,伸手去抓时,指尖刚碰水面,鱼群就“嗖”地散了,只留下一圈圈涟漪。红蜻蜓停在芦苇尖上,翅膀颤巍巍的,手刚伸过去又“呼”地飞远了,裤脚沾了泥也不管,满脑子都是瓶里游来游去的蛤蟆骨朵。
下午日头稍斜,蝉鸣渐渐稠了,“滋啦滋啦”缠在树梢,把空气烘得更热。水面被晒得发烫,叫花哥和伙伴们才恋恋不舍爬上岸,光着黑黢黢的脊背往家走。我提着装蛤蟆骨朵的玻璃瓶跟在后头,刚进院门就被外婆逮住。她准会攥住我小腿划一下:下水的孩子腿上沾着水汽,划过留道白印;没下水的就没有。我紧张地盯着她的手,她却笑着捏我脸:“乖娃,没下水就好,不跟你老表疯。”那点藏在慌张里的安心,如今想起来比城壕的水还暖。
这城墙对我们来说是独一份的便利。热得受不了时,就往上面爬,风裹着野蒿的气息呼呼地吹,蒿叶在风里摇得欢,吹得人浑身燥热散了大半。夏天下过雨,墙缝里还能捡着地软,黑黢黢的一小团,捡回去让外婆掺在面里蒸包子,那香味能勾着人多吃两个,香得忘乎所以。
城墙偏西的南壕是个特殊的地方。那是个一米多深的坑,约莫有半个足球场大,过去常有犯人在这里被处决。
有年秋天,听说要枪毙人,县中队的战士早早就设了岗,岗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里三层外三层的。我们却不着急,悄悄爬上城墙,居高临下地等着,这视角可比底下清楚多了。
果然,没过多久,就见县中队的战士一边一个搀着三个罪犯,拖着走进南壕的野地里。战士们喝令他们跪下,三个罪犯便并排跪在了地上,侧身正对着我们这边。他们身后,另几名战士端着枪,枪口稳稳地对着他们。岗里有人喊“预备”,这时那面红旗“唰”地举起来,在空中停了片刻,我的心跟着揪紧了,攥着城墙土的手也更用力了。就在“放”的口令刚落,红旗猛地向下一落的瞬间,“砰砰砰”三声枪响炸破空气,连在一起像炸了个响雷,震得耳朵嗡嗡响。跪着的人一起往前扑了扑,直挺挺趴在了地上,有一个似乎还动了动。
岗里负责监刑的人走过去,手里提着一把手枪。他看了看那两个没动静的,没说话,转而对还在动的那个,抬手补了一枪,“砰”的一声,比刚才闷些。
岗外的人嗡嗡议论,我们手心里全是汗,谁也没说话。攥着的城墙土顺着指缝往下掉,直到岗哨撤了大半,才发觉掌心已被硌出几道红痕。
天渐渐黑透了,蝎子、簸箕虫耐不住热,从城墙的土缝里、小巷的砖缝里、门道的石缝里钻出来乘凉,这正是抓它们的好时候。我和老表各提一盏马灯,灯柄攥在手里,用另一只手拎着带铁盖的罐子,镊子就捏在拎罐子的那只手里,谁也不跟谁的趟子,各找各的目标。
他眼尖,瞅见砖缝里翘着个蝎尾,立马蹲下身,把马灯往地上一放,腾出的手接过镊子,动作又快又稳。蝎子“噌”地被提出来,手腕一翻就丢进罐里,“啪”地扣上盖,嘴里还嘟囔:“又一只,今晚能多换两颗糖。”我也不示弱,举着灯在墙根扫,看见簸箕虫从石缝里爬出来,赶紧蹲低了,把马灯搁在脚边,捏着镊子的手慢慢伸过去,趁它没缩成球,稳稳捏起来丢进罐里,盖好盖才松了口气。蝎子我也敢抓,瞅准了猛一夹,哪怕手有点抖,也得让它落进罐里。
俩马灯的光在黑夜里晃来晃去,他的罐和我的罐时不时“咔啦”响一声,那是蝎子爬、簸箕虫撞的动静。谁也不耽误谁,各抓各的,像是在比着赛,又像是各忙各的正经事。
回到家,我把罐里的“战利品”倒出来,用开水烫死,清水冲净,撒盐腌着;叫花哥在他家,想必也是这般操作。第二天,我把腌好的摊在自家竹筛上晒,他那边估计也正晒着。太阳把水分抽干,我筛子里的蝎子缩成褐色小团,簸箕虫硬得硌牙。等各自攒够了量,就揣着往药铺跑。
柜台后的人总抬眼皮扫一眼,慢悠悠问:“哪的?你爸叫啥?”老表眼珠一转,瞎编个名儿,声音含含糊糊的。我早想好了说辞,憋着笑答:“我爸叫乔饸饹。”说完赶紧低头,趁那人低头划本子的功夫,飞快扭过头冲叫花哥挤了挤眼,嘴角憋不住地往上翘,他也正瞅着我,俩人手都还攥着盛虫的袋子,肩膀却一起一伏的,偷偷笑出了声。
那人把一块多钱递过来,我们接了钱赶紧往外跑,刚出药铺门,就“噗嗤”笑出声来。叫花哥拍我胳膊:“你爸叫乔饸饹?亏你想得出来!”我也乐:“总比你瞎嘟囔强,他压根没听清!”俩人揣着发烫的钱,一路跑到供销社。
柜台后的大婶正扒拉着账本,见我踮脚趴在柜台上,头也不抬地问:“要啥?”“买豆豆糖!”我赶紧应道。她抬眼扫了扫我攥着钱的手:“糖票呢?”
我赶紧凑上前:“大婶,就买三颗,一毛钱,不用票行不?”“没票不卖。”她低下头继续划账本。老表在旁边拽我衣角,俩人蹲在柜台边磨:“大婶,我们攒了好久的钱,就想尝尝甜的”“就三颗,下次我们一定攒票来”。磨了好一会儿,她叹口气,接过我递过去的一毛钱,从玻璃罐里数出三颗豆豆糖,红的、绿的、黄的各一颗,直接倒在我手心里:“赶紧揣好,别让主任看见。”
攥着那三颗光溜溜的豆豆糖跑出门,糖粒硌着手心,黏糊糊的。我小心地用纸把黄的那颗包起来,塞进裤兜,这是留给二哥的,他虽总欺负我,可我们毕竟是兄弟。剩下的两颗,我和叫花哥分着塞嘴里,脆甜的滋味在舌尖炸开,连带着刚才的紧张,都成了说不出的香。那点藏在拮据日子里的甜,比啥都让人记挂。
每晚,当我回到家,把这些蝎子、簸箕虫收拾停当后,就见外婆已在院里支好了大床。她见我走过去,就拍着床沿催:“快洗把脸,赶快睡吧。”我和大哥二哥挤上去,她摇着蒲扇,风里混着城壕的水汽,一边扇着蚊子,一边把暑气扇走大半。可我怎么也睡不着,便拽着外婆的衣角晃:“婆,给我讲个故事吧。”外婆低头瞅了瞅我,蒲扇慢了半拍,笑着应:“那我就给你讲个‘雷打张继宝’吧。”
这故事最吓人,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说张继宝不孝顺,做尽坏事,最后被雷公公追着劈。我们缩着脖子听,大气不敢出,怕自己学坏了也遭报应。外婆就抬头对夜空念叨:“我娃都乖,学好,雷公公不劈好人。”那时信以为真,觉得她的话是给我们求来的护身符。星星在天上眨着眼,蒲扇摇啊摇,把故事摇得慢悠悠的。
那时,我和二哥总爱打架,鸡毛蒜皮的事都能吵得脸红脖子粗,有时还会滚在地上撕扯。外婆拄着拐杖劝,嗓子喊哑了也没用,常常急得直抹眼泪。有一天,我俩又为抢一个玻璃弹珠打起来,二哥把我推倒在泥地里,我哭着揪他的头发。外婆突然不劝了,转身回屋慢慢梳了头,换了件干净的蓝布褂子,出来时脸色平静得吓人。她望向门外,声音轻轻的:“你们继续打吧,我也不劝你们了。我去三队饲养室那,跳井去,眼不见心不烦!”
我吓得瞬间忘了哭,连滚带爬扑过去抱住她的腿,二哥也“哇”地哭了,拉着她的胳膊直摇头。“婆,我们再也不打了!”我抽噎着说,“我让二哥先玩弹珠,我啥都听你的!”外婆这才蹲下来,一手搂一个,眼泪掉在我们头上:“要学好,兄弟得和睦,不然长大了没人疼。”那以后,我和二哥果然很少再吵,偶尔红了脸,只要想起三队饲养室那口井,就赶紧各退一步。
舅大的桑树在后院,碗口粗的树干,枝叶长得繁茂,能遮半院阴凉。夏末时,红得发紫的桑椹挂满枝头,沉甸甸的,甜汁几乎要滴下来,看着就让人眼馋。外婆总劝我们:“别翻墙去摘了,让人看见不像样。”可我和二哥哪忍得住?趁她不注意就溜到后院,踩着墙根的砖缝往上爬。舅大为了防我们上桑树,特意在树干上抹了湿乎乎的大粪,臭味熏得人皱眉,可那点味道哪挡得住俩小馋虫?等大粪风干了,我们照爬不误,抓起桑椹就往嘴里塞,甜汁顺着喉咙往下淌,沾住嘴唇和牙齿,连指尖都染成了紫黑色。
外婆在后院撞见好几回,没骂我们,只叹口气。转年春天,她在羊圈旁挖了个坑,栽了棵小桑树苗。扶着树苗,她对我说:“以后别翻你舅大的墙摘桑椹了,咱自己栽,争这口气!”那棵小桑树长得慢,可当年夏末就结了几颗桑椹,酸里带甜,摘的时候刺到手,疼也顾不上。我知道,那是外婆怕我们馋嘴,更怕我们让人笑话,悄悄种的体面。
蝉鸣渐渐稀了,玉米秆已没过膝盖,后院茅厕旁的枣树上,熟透的果子红了。碗口粗的树,挂满了玛瑙似的枣子。父亲会先拿铁锨铲黄土,仔细盖好茅厕里的粪便,再抄起竹竿往树枝上敲。红枣“噼里啪啦”落下来,砸在我们张开的衣襟里,带着阳光的清甜味,硌得胸口微微发疼也高兴。他举着竹竿的胳膊酸了,换只手继续敲,后背的汗湿了一片,在风里慢慢凉下去,像给秋天按下了开关。
夏天的午后,知了叫得最欢,“滋啦滋啦”像无数个小喇叭,把热空气填得满满当当。我们举着自制的网兜,在树林里追着声找,网住了就捏着翅膀回家。到了锅间,往灶里塞几把干柴,“噼啪”燃起一小堆火,把知了蘸点盐,裹层湿泥巴丢进去。等泥巴烧得干裂,剥开时焦香直钻鼻子,连壳带肉嚼着,香得能把舌头吞下去,手上沾着的泥渣都想舔干净。
入了秋,玉米地开始热闹了。蛐蛐“叽叽”地叫,调子比知了柔缓,带着点清冽的凉意。我们钻进齐腰深的玉米秆里,被叶边的锯齿划了道子也不管,扒开叶子找蛐蛐。抓到的装在泥星罐里,用麦麸子喂着,凑在一起斗仗:用细草棍逗它们的须,看两只小虫子张着牙互咬,赢了的那只,能当“将军”供好几天。玩死了就丢给鸡群,看母鸡扑腾着抢食,倒也不觉得可惜,只想着明天再抓一只更厉害的。
这些散落在夏末初秋的片段,原以为会随岁月蒸发。可昔日的城壕被填埋,盖起了农家院落;曾经的玉米地,也竖起了栋栋楼房。外婆的蒲扇、父亲的竹竿、老表的笑声,终究被时光带去了天堂。
直到某个蝉鸣扯着热意的午后,指尖触到桑椹紫黑的黏甜,才猛地醒过神来。岁月会老,会被新砖瓦压进尘土,但那些藏在里头的爱——外婆划我小腿时的担忧,是怕我贪凉落水的疼惜;父亲举杆为我打枣的身影,是把甜意都往我怀里塞的宠溺;老表在浪花里的笑闹,是孩童间最纯粹的欢喜,早成了心湖里的锚。
这爱,是刻在骨头上的念想,是走多远都甩不掉的牵挂。任岁月怎么淌,这思念都晃不散、磨不掉,成了这辈子永远揣在胸口的重量,沉甸甸的,带着他们的温度,陪我走过往后的每一个夏秋。
责任编辑:林白
2025-08-15 08:58:51
2025-08-15 08:36:35
2025-08-13 22:09:12
2025-08-13 14:05:56
2025-08-13 09:30:52
2025-08-13 08:51:03
2025-08-11 11:58:51
新闻动态
公益明星
榜样人物
草根故事
热门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