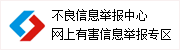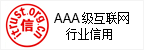水魂一曲长天歌 ——序《爱河》
与一个时期甚多的作品将时代、背景、事件、具体环境故意模糊淡化的做法相反,梦萌长篇小说《爱河》的时代、背景、环境却是十分清晰的,他自己也不讳言这是写“文化大革命”中重新上马、完工的宝鸡峡水利工程的。但这并没有妨碍《爱河》的艺术成就,并没有妨碍它已经作为一个美的艺术工程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这里面有作为一个美的创造物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有作为一个艺术品所必备的作者的生命和真诚,有一代又一代人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对于美好的生活理想、人格理想的追求。
说来也巧,我的家乡就在《爱河》所描写的关中西府,这里虽不是宝鸡峽工程的直接受益区,但这里的父老乡亲像作品所描写的泾河之尾的龙尾村的人一样,也自始至终参加了这场感地动天的水利会战。先是1959到1960年的困难时期,自己的邻居,自己的叔伯兄弟们,也常被派往宝鸡峡工地,往往一个还算健康的人,几个月一回来就神情凋敝、失颜变色,俨然释放的苦役一般。常有某个社员不听话,书记、队长就说:“让他上宝鸡峡去!”以后就听说因为国民经济调整,宝鸡峡工程下马停工。文化大革命中,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宝鸡峡工程又复工上马,这次会战所动员的人力之广,连当了小学教师、有了一个孩子的笔者的妻子也去参加了。她是一个没有文学细胞的人,回来也没有发表什么感想,只讲了驻地人的热情和劳动的繁重,但是神情上再没有当年叔伯们的凋敝了。至于宝鸡峡工程的整体面貌,它对渭北,乃至陕西农业生产发展的意义,我也只是在读了《爱河》以后才有所了解的。
与笔者对宝鸡峡工程的陌生相反,《爱河》的作者梦萌却是这项造福于后代子孙的伟大工程参加者。他居住在世代干旱的咸阳原上,文化大革命初期辍学返乡务农,宝鸡峡工程重新上马以后,像作品中的沈平一样,他带领数百名由农民、返乡知青、城里下乡知青组成的民工队伍开赴汘河,投入了工程的建设;尔后又担任了工地宣传干事,办简报、广播、文艺队;再后便成了一名正式的水利职工,至今仍工作在水利战线。像梁晓声之于北大荒,史铁生之于陕北农村,孔捷生之于西双版纳,朱晓平之于桑树坪,宝鸡峡工程的十多个春秋,也在梦萌的心田打下了深刻的印记,使他魂牵梦绕。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的:“二十年来,每当人们抱起一个个沉甸甸的秋和夏,便不由想起那一段不平凡的岁月,想起那一个个动人的场面和一件件可歌可泣、催人泪下的故事。……那许许多多熟悉的人物仍鲜活地浮现于脑,直闯入梦,使我产生一个大胆的冲动:拿起笔来,把他们写出来!”但是,对于一个水利技术干部来说,实现梦想又谈何容易!为此,他又以一个农民儿子的坚韧,开始了在文学道路上的漫长跋涉,他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写短篇小说;跑编辑部投稿,退了,再写再投;拜文学的行家里手为师,考入西北大学作家班深造……终于文学的大门在他面前敞开,艺术创造的成功向他发出动人的微笑,继十几篇短中篇小说、数十篇报告文学等之后,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爱河》终于脱稿。仅从《爱河》出自于一个技术人员之手这件事,我们就能感觉到作者那如泾、渭水般从两岸的高原丘壑、肥田污土吸收了充分营养的奔腾不息的激情,长流不断的柔韧,永远向前追求。
恐怕只有作者自己才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这其间有多少不堪忍受的悲哀与酸辛!当作者把九百多页的书稿经由出版社编辑的审查,又送到笔者的面前的时候,我仍然能感到他那对自己的创造的激动和不安。
比起成熟作家的精心之作,《爱河》当然更有许多可以挑剔的地方,但是我仍然认为即使放在严肃的文学天平上,它也是很有价值的好作品。这里虽然没有宏大的史诗规模,但却有一个伟大工程中的新鲜生活和令人耳目一新的人物;这里虽然没有巨大而深刻的思想和先锋意识,但却有只有亲历者才会有的生活热情和描写的真切;这里虽然没有可称“尖端”的技巧和手法,但却有不乏感应着时代审美风尚的独特的艺术感觉和大胆的艺术想象。
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特殊的背景下,宝鸡峡水利工程重新上马了,尽管一时占了上风的帮派理论家们把它说成是对刘少奇批判的结果,对“走资派”斗争的胜利,但实际上领导、参预、支持这个工程的却是当时处境极为艰难的老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下乡和返乡的知青,以及广大的农民,而以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为目的的“四人帮”的爪牙们却百般地破坏和干扰。宝鸡峡工程工地的斗争,既是当时全国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又有自己的特殊形式。《爱河》以朴素的笔触展现了这不幸年代的激荡人心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这一昂扬的时代主题。但是,作者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沿着这个方向开掘下去,寻找着决定这场斗争人民胜利的更深层原因。这就是由远古时期的大禹治水,中经秦郑国渠、汉白渠、唐三白渠,到民国的泾、洛、渭惠渠,乃至人民解放战争中的西府战役所以一贯之的前人受苦、造福后世、勤劳、务实等民族传统精神。正是这个伟大民族的不朽的精神风范和光荣的斗争传统,铸造了宝鸡峡工地这些年龄、经历、生活地位各不相同的战士和英烈们的不屈的灵魂。特别是那些被排挤出领导岗位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更为感人,他们不顾个人安危,顶着重重的压力和凶险,站在了历史的最前列。陆政委、老专员、章指挥、刘总工程师,都是这些充满着民族的光辉和精神的共产党人形象。他们是人民的儿子,是人民哺育了他们,给了他们力量;他们又是人民的杰出代表,人民的领导者和代言人。他们同沈平、塌鼻五叔、珍珍、诸三猫、张狗团等相濡以沫,患难相随,休戚与共的关系,构成了《爱河》这部爱的乐章的主旋律,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主旋律。这种主旋律,这种主题,或许要被人讥之为陈旧,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了更大的现实意义,才值得为之叫好。
水,这个地球表面最多的物质,在这些年才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但这种关注只是当人们意识到它已经被污染,被浪费,从而已经匮乏到威胁人类生存的时候。而水在《爱河》中却成为一个独特的意象。人类缘水而生,而人类有史可载的第一个英雄又是因治水而引起后人的无限敬仰。由他而始,中国历史和民间传说中与水有关的治世人物,也分外能获得人们的普遍尊敬;而翻遍中国的诗词、绘画,歌颂江、河、水也似乎成为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美。能见于这一切,不只来自梦萌作为一个水利工作者的职业的自豪感,还来自于他对水与人民生活、社会发展关系的独特的认识。“水浇灌着我的诗心。我便是水,水便是我。我虔诚而执着地追求水的性格和风格。”水之于梦萌,已经成为对象化了的自然,成为美的理想和人格的理想。它表现为心头永远呜响着母亲的呼号和沈平的以水利事业为自己的生命,也表现为如山猫、狗团这样的野性青年在水面前的忘我和沉静……“水魂一曲长天歌”,《爱河》正是一曲响遏云霄的当代的水魂之歌。沈平的母亲是死于水的,珍珍的父亲是死于水的,身上背负着永远诉不出的个人屈辱和苦难的王淼姑娘是为了水而触及法网并最终死于水的,而沈平的死虽然惨凄,但却未必不是他所向往的,——他将自己的血肉碾碎了,铸进大坝的泥土之中。而水又孕育着生命和爱情,在文化大革命那禁锢生命和爱情的年代,是水库周围的山洞容纳了婉婉的新生儿,是如水的月夜成就了沈平的爱情,是水利工程促成了狗团和二品这对不幸人的婚姻,……古今有多少人写水、写河、写江、写海,然而又有多少人能象《爱河》这样,理性地思考过水,穿越历史空间地俯瞰过与水有关的人和故事,又有多少人赋予了水既浪漫又现实的灵性,写出了水的灵魂、水的神韵、水的品格。这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广大水利工作者的骄傲。
毋庸置疑,《爱河》作者具有文学艺术家的灵性和才气,他的想象力是大胆而奇诡的,他的笔触是流畅而浪漫的,前面已经说过,它来源于作者对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群众的深厚的感情,来源于对家乡土地的历史和现实的深沉的爱,来源于水利职业的自豪感和永不满足的求知欲望。《爱河》是一曲动人心魄的爱的颂歌,且他没有回避生活的困难和人生的严峻,也没有刻意去美化和拔高自己钟爱的男女青年,而是如实地写出他们坎坷的人生历程、生活道路、复杂的性格。沈平曾经是一派红卫兵的头儿,干过亲痛仇快的事情;诸三猫也曾经是一派群众组织的干将,即使在水利工地上,他和张狗团也时时流露出封建行帮式的流氓无产者习性。至于王淼那就更为复杂了,她曾经是单纯可爱的,但在遭坏人奸污后,产生了对生活强烈的报复心理,她对沈平的爱在作品的特殊环境下,可能是真诚的,但作者同时也暗示了这也是对极左路线下的人性禁锢的报复,是一种空虚心态下的自爱,是对自己把握不了的不幸命运的抗争。如果说沈平、珍珍等青年对水利事业生命的投入是对一种理想的追求的话,那么王淼、山猫这些复杂性格的把握还缺乏一定自觉,缺乏更深入的分析和理解,但他们毕竟作为特定时代、特定背景下的人物真实地站起来了,给人以震撼,给人以思考,折射出较为丰富的生活内涵。
在作者给以更多的否定和批判的形象中,潘欣生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成功之处也在于作者没有把他简单化,而触及了这个性格复杂的成因。他继承了家族传统中恶的因子,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又得到了极端的发展,这就是只要有利于自己向上爬,不惜出卖、陷害恩人和朋友。政治投机是文革中的时代病症,他于此可说是得心应手、轻车熟道。然而比起哥哥潘雨生他毕竟多读几天书,在出卖良心的投机中裹上了一层文明的面纱,在干坏事中有时还受到良心的拷问。他的支持王淼遗体进村,以及反对哥哥启棺、撕毁逮捕证等,乃至最后因沈平惨死刺激而神经错乱,就说明了在正常情况下,这种人并非一无可取,不可救药。同王淼、潘欣生,甚至山猫、狗团等比较复杂、性格心理打上更多时代和历史的烙印的人比,作者对沈平从一个红卫兵头儿到忘我的水利战士的心灵历程却揭示得不够,缺乏必要的层次性。虽然如此,在书中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带有作者理想色彩的青年英雄形象,他有知识,热爱生活,懂得爱情和友谊,继承着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美德,显示了中国的希望和光辉的未来。
承梦萌同志抬爱,诚心诚意地请我为《爱河》作序,而我却因为诸事缠绕,不能更为精细地研究作品,以上意见只能当作一个第一批阅读了作品的读者的不成熟的思考,如能对以后阅读这部作品的读者朋友有些微的启发,也将是我最大的荣幸。谨祝梦萌同志以此为起点,以一如既往的精神和毅力,谱写出更美更动人的水魂之歌!他具有这个条件,有不会令人失望的巨大的潜力。
(原载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爱河》,后刊于《小说评论》和收录于多种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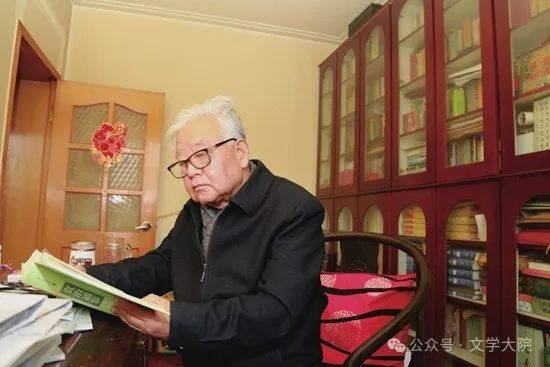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李星196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专业。历任《陕西文艺》《延河》杂志编辑,《小说评论》杂志编辑、主编,编审,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时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陕西生态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陕西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影视评论学会常务理事。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出版文艺评论专著多部。
责任编辑:韩雪
2025-07-09 22:09:20
2025-07-09 22:05:38
2025-07-09 11:29:06
2025-07-09 11:27:56
2025-07-09 11:27:01
2025-07-09 11:07:22
2025-07-08 12:26:50
新闻动态
公益明星
榜样人物
草根故事
热门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