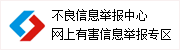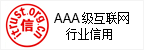精神家园的重构与作家的城市描绘——读梦萌长篇小说《倾城》
在陕西作家群中,梦萌是较早涉足城市题材的老作家。本世纪初,他曾经以一部《悲喜娱乐城》而对商品大潮下城市的浮华和沉糜做了深刻的文化批判,近日,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倾城》,是他的第二部城市题材作品。作家不仅保持了在《悲喜娱乐城》中所坚守的文化批判精神,而且赋予眼下的作品以深沉而又凝重的人文情怀、温暖而又苍凉的悲悯精神和残酷而又惨烈的悲剧色彩,从而在艺术的层面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他对于城市描绘的新突破。
读罢《倾城》,掩卷沉思,我油然想到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都在苦苦思索的一个严峻的课题:这就是工业或者后工业时代生命所存在的那种“新时代的无家可归的状态”。因而,如何构建能够让漂泊的灵魂得以安妥的精神家园,就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一种带有当代意义的使命和责任。这也正是《倾城》的价值所在。
一
对于梦萌这样有着丰富人生阅历、漫长艺术实践的作家,“怎么写”固然始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话题,然而,在我看来,写什么,更是关系到他作品审美价值的现实选择。梦萌对此有着清醒的文化自觉。他一直试图突破陕西作家在乡村叙事的道路上拥挤徘徊的窠臼,而将叙事的笔触伸向城市。
他的这种选择打着自我文化基因的深刻烙印——其与乡村的血缘纽带决定了,他总是以一个外来者的目光去看待城市的变迁演进。因此,活跃在《倾城》中几乎所有的艺术形象,从麦氏父女姐妹到美兰、南楠的命运图谱,都可以从乡村到城市的环境转换中找到内因,而不同于上海、京津作家笔下的“城市”开掘。
在作品中,弥漫着道教文化氤氲的全真镇,曾经在一种传统的经济模式和生存方式下绵延着它的散淡、稳定和温馨,然而,有一天,城市经济转型的波浪终于引起了这个依赖于为国有厂加工火柴盒的小镇的“阵痛”,当麦轵和他的儿女们被以送货为由诱骗到城里而误入示威队伍时,他们终于明白,他们生命的脚步不可能再沿着旧有的轨迹继续,而面临着一场破茧成蛾的巨变。老镇长因二女儿麦珊被抓而昏倒在政府门前,是作家颇具哲学意味的铺垫。它既是一曲旧生存方式的挽歌,又是生命新的嬗变的序曲,更成为作家笔下人物走向城市的命运起点。麦轵病愈后回到了乡村,而他的女儿和她的同龄人却选择了城市。
那么,这个陌生的环境对于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正是在这个节点上,表现出作家梦萌对现实的文化批判力度。一方面作家笔酣墨饱地描述白天城市的繁盛和华美、时尚和风流、拥挤和匆忙,以及到处隐寓商机的蓬勃和雄劲;另一方面,在温柔、温情、温馨的夜色下,借助于男主人公全皓的目光,一点一点地撩开城市神秘的面纱,把它沉沦和惰性的一面展现在读者面前:那些徘徊在钟楼下的“三陪女”淫荡的笑声和穿梭的身影,那些盘桓在五路口立交桥“鸽子架”上靠“出卖肉体和灵魂”生存的“野鸽子”们……让全皓遭遇了道德与人性的尴尬。一方面,是穿越千年青史,留下儒、释、道人文景观的都市辉煌;另一方面,是浑浑噩噩的现代政要们拥着羽衣霓裳的舞女,在纸醉金迷的沦落中演绎着权利与肉体的交易。一方面,人前言之凿凿,道貌岸然;另一方面,私下里却蝇营狗苟,廉耻丧尽。在作家的审美视野中,城市就是一方多色调的大舞台,每日上演着荣与衰、美与丑、善与恶、阳光与阴暗、真诚与虚伪的岁月轮回,从而为故事铺开复杂纷纭的文化背景和矛盾交织的人文环境。
带着传统文化基因走进城市怀抱的麦轵二女儿麦珊和与她一起登上青春渡口的麦兰、小钱和南楠们,由于缺乏在城市文化机体上的抗体,使得他们从父辈那里承袭下来的人生经验和道德理念,在一种新的文化生态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灵魂很快被“利益”和金钱所俘获。从最初的正经做生意到钻政策不完善的空子办皮包公司;从靠色相打通秘书长的关节到拿来牛仔布厂的订单再到兴办华洋工贸公司,趋利行为极度地挤压着麦珊的人性,她把美色当作可以交易的资源,不但在董事会上与秘书长达到钱色交易的默契,而且最终发展到上床合欢。人的灵魂“耻感”就这样地被一层一层地剥噬掉,只留下赤条条的裸色。
如果说,在麦珊那里,“漂亮也是资本,而且是像美元一样在世界范围内通兑的货币等价物”的价值观带着浓郁的商业趋利行为,那么,美兰因为与嫖客“口交”而染上性病直到最后堕落为一个骗子的行为,则让我们强烈地感到,一种堕落的文化是怎样把一朵带露的鲜花异化为社会毒瘤的。美兰不仅自己白天睡大觉,晚上陪酒,而且劝麦娜也去傍大款。在她的价值天平上,三陪小姐“来钱容易得只是举手之劳。还有那些傍上大款的人精,更像猴儿变脸,两三年就有了房子有了车,摇身一变成了中产贵夫人。”这种体验虽然显得浅薄而又粗鄙,却深刻地揭示了某些“财富聚集者”完成原始积累的秘密。它让我们再一次思考,什么是“现代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我们究竟应该在物质富裕的时候,拥有怎样的灵魂栖息地。美兰的悲剧,从本质上说,是文化的悲剧。
要么,从城市的怀抱崛起;要么,在城市的魔方中沉沦。
要么,在文明的沐浴下构建新的精神家园;要么,成为没有灵魂皈依的“新时代无家可归的人”。
二
在当代中国,任何作家的城市叙事,都不可能绕过经济体制变革这个现实,或作为叙事的主体,或作为人物思维和行为的背景。
全真镇的旁落,缘起打火机的冲击,属于生产力范畴的矛盾,充其量只是故事所以发生的由头,梦萌的深层开掘还在于,当全真镇的年轻生命进入城市,并且有机会成为传统体制内底层的一员时,所遭遇的是人与环境的冲突。
对于梦萌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很大难度的挑战。因为,在理论层面,城市经济体制的变革和机制的转换,是上世纪中国自乡村改革后最为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它对于城市生产力解放,城市形象再塑,城市品格锻造,城市文明进步的推动是前所未有的。它从开启航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受到作家的关注。然而,数十年过去,当我们回头再去检索那些在当时曾经引起轰动效应的作品时,就不难发现,除了图解政策外,很少有人触及它怎样带给不同利益群体的多元“痛感”,特别是社会底层那种生存危机的“惆怅”;很少去反映当他们被潮流裹挟,忽然失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时的那种仓皇和无奈;很少去关顾他们在承担“阵痛”代价时那种忍辱负重的品格,这就使得这些作品缺乏一种历史的厚度。
正是在这一点上,梦萌实现了题材维度上的新突破。它以帆布厂的体制改革作为文学意义上的典型,把经济转型的复杂曲折和深层矛盾呈现在读者面前。于是,我们从人物的沉浮悲欢中读出,当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力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一旦与权力的腐败纠结在一起时,就把本质上给民众带来福祉的性质异化为一种底层社会的“苦难共担。”
作家长于先扬后抑,在悲喜起伏中展开人物的命运历程。被传统体制束缚了几十年的男主人公全皓和他的哥儿们,对帆布厂改为牛仔布厂寄予了满腔的热情和期待。正是在这一片灿烂的光环下,全皓千方百计将本来对城市充满仓皇和不适的女友麦娜招进工厂。他们爱情的小舟,伴随着事业的旋律,划出层层碧波。他们在劳务局管印章的老熊门口等他,忙中偷闲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肌肤之贴、唇舌之吻,品尝到爱情的温馨。“两个恋人就这样紧紧拥抱在一起,心里都感到无比快乐和幸福。他们忘记楼外的大雨,忘记楼上的老鼠和麻将声,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人和他们甜蜜美好的爱情。”那一刻,他们除了感恩,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切背后,一直有一双权力的手,掌控着生活的魔方。直至工厂开业那天,呼风唤雨的秘书长突然出现在典礼现场,后来麦娜被厂里抽去陪酒,狂欢中的人们依然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去思考眼前的光敞琉璃竟然会发展成他们命运的“陷阱”。当保全工八号栾奕发现所谓的进口设备,竟然有许多零件是国产货时,却也没有引起全皓和麦娜的警觉。作家借助于这个细节,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这场表面上轰轰烈烈,而实际上为秘书长暗中操纵的假引资和被严重扭曲的所谓改制,终于在麦娜、全皓和南楠的情感纠葛中,在被爱折磨得“痛并快乐着”的苦旅中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更可怕的是厂子真的破产了,真的要拍卖了。”工人们开始静坐,全皓没有去,受到工人们的责骂。厂里买断工龄兑现大会那天,他也没有去领按工龄折算的三万多元,而让麦娜去代领。城市就这样将他们从温暖的怀抱抛向人生新的十字路口。
城市因为多了一群漂泊者而显得步履沉重。
它首先打碎了工人们殷殷以待的憧憬。麦娜和全皓不得不用自行车驮上滞销的牛仔布,走街串巷地将之换成工资。对于全皓来说,工厂破产后的诅丧、被工友的唾骂、对麦娜“未见红”的耿耿于怀、以及无所事事的焦虑,环环绕绕地折磨着他的情感,使他的心灵大陆极度倾斜,将理性挤压到狭小的空间。与其说,他借着酒胆到曾经强暴了麦娜的南楠店里寻求报复,毋宁说,这正是主人公精神世界坍塌的宣泄。
它也将麦娜苦苦修复的爱情红线再度剪断,将两个相爱着的青春生命推向情感的两极。全皓因为处女膜的疑窦而对麦娜的冷漠,又因参加二姐婚礼得以复苏。“全皓的生理障碍已不复存在,他的生命的韶华反过来又成为麦娜火样青春的寄托和安慰”,并且成为他们筹备结婚的动力。然而,工厂的破产,使他们重新启程的爱情列车再度抛锚。终于有一天,全皓决定离开麦娜,告别这座给他留下很多忧伤的城市,回到苏州去寻找新的生存出路,从而把自己由肉体到精神都变成了一个毫无责任感的孤独的流浪者。
它将沉醉在爱河中而又对全皓怀着深深负疚的麦娜推向生存和守望的困境。她苦苦等待着心爱的恋人,突然发现自己怀孕,有了爱情的结晶;她瞒着父母欺骗二姐,顶着世俗的讥讽和压力,迎来呱呱坠地的非婚的新生儿;她为了抚养儿子,不得不到曌皇大厦去当舞女,赚钱养家糊口;她在遭到性骚扰后,又重操旧业,为药厂糊药盒……终于,在被美兰骗取全皓留的4万元之后,她于绝望中找到秘书长,把自己的肉体和精神都交给了她。直到五年后,她与全皓重逢在古城时,才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秘书长预设的套子。尽管这位弄权者为自己的虚伪、阴暗和肆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他留给读者的思考空间却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深度。
以我有限的阅读经历,像梦萌这样从腐败权力扭曲改革本质属性,而又让社会底层承担代价的视角反映城市题材的小说还不多。诚如鲁迅所说,悲剧就是把世间最美的东西撕破了给读者看。《倾城》所弥漫的悲剧色彩,从两个层面表现了作者开掘生活的力度。首先,造成全皓和麦娜悲剧的客体因素是权力扭曲而导致的社会震荡。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不乏像牛仔布厂这样的国有资产流失改革失败的案例,但有着光荣传统的产业工人却以历史主人的自尊校正了航道。所以,悲剧内因还在于他们对于精神和信念的坚守缺乏文化的自觉,还在于信仰家园的荒芜。
三
在《倾城》中,城市有着自己固有的文化品格,精神理念,滋润着千年文化古道,也滋养着她怀抱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塑造着她的儿女丰富的性格特征。
所谓城市品格,是由一座城市的历史积累起来的人文生态、文化气韵和道德氛围,是物质关系以及建立在物质关系基础上的生活关系、精神关系。它具有历史传承性、现实广延性和主体趋向性,构成一个城市与它毗邻城市的个性差异,成为艺术作品中人物性格形成的渊源。
尽管梦萌在《倾城》中对城市变异中的喧嚣和媚俗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但这并不妨碍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作品中人物赖以生存的城市投以审美的目光。作家很深情地设定了麦轵在连副大爷陪同下游览古城的情节,汪洋恣肆地描绘作为十三朝古都和京畿之地带着悠远富集的文化资源、精彩纷呈的人文遗存、千姿百态的民俗风情。一座座古塔闪烁着人类的思想光束,一道道古城墙回荡着金戈铁马的涛声,一通通碑石镌刻着智慧的密码,正是这一切,奠定了古城辉古耀今的价值地位,使它即使在市场经济时代仍深深地影响着城市主人的思想、情操和人格品位。
这里是爱情的港湾,她缔造了麦娜和全皓这一对苦恋的爱情鸟。麦娜是作家倾注饱满激情和淋漓笔墨塑造的艺术形象。她性格的主导性源自于知识分子父亲的耳濡目染,源自于全真镇浓郁的传统文化熏陶,而她性格的丰富性却是城市给予的。前者使她在刚刚进入城市时,“走在大街上,就像一只北方的麻雀或黄鹂误飞在大海的上空,充满着惊讶、惶悚和困惑。”后者则赋予她守望爱情的品格。那站在城头默默遥望远方云彩的目光,那久久伫立在“望夫台”上的孤独身影,那执拗地为了爱情宁可与情人抱着亲着跳城自尽的迷狂情态等,都让我们感受到城墙作为诗意意象,与主人公互入互化、“物我为一”的乖戾和悲凉。
城市品格的核心是“人”,人创造了城市的高峨,它又反过来雕凿着人的行为。麦娜周围的人很多,但直接对他构成感染的还是连副大爷这个人物。作家对连副大爷着墨并不多,但却是城市襟怀、城市善性的代表人物。他不但强烈地影响了全皓,更深深地向麦娜传递了这座城市穿越千载的道德品行。他多次在麦娜陷入困境时给予她以襁褓式的温暖和安定,从而在麦娜的潜意识中形成自尊自爱、宽容诚挚的性格,使她在面临爱情危机时,拒绝二姐要她用红墨水代替女儿红欺骗全皓,拒绝二姐要她打掉腹中胎儿而呵护了爱情的结晶,并且在一片浮靡躁欲中,守护着属于自己的道德底线;当美兰坠入苦海时,她向她多次伸出援助和拯救之手。她之所以能坚守到与全皓相逢,与连副大爷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他催化了麦娜性格主导面的养成。然而,另一方面,她和全皓爱情的悲剧,除了外部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他们各自的性格弱点,如麦娜在情感上小鸟依人的“黏黏糊糊”,全皓计较细节的患得患失等。这样,无论是男主人公还是女主人公,便都成为真实的具有“浮雕感”的艺术典型。他们既负载着变革时期的“社会矛盾”,又以在作品中保持着鲜明的个性而成为与过去城市题材作品中毫不重复的“这一个”。
这里弥散着人性的温馨,使得真善美穿破世俗和流俗,在生命主体的灵魂碧野上浇铸起人格的高塔。当作家将艺术触觉伸向普通小人物时,他们的敏锐和胆识、善良和大度,使读者感到,他们才是这座城市的脊梁,他们的人格殿堂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灵魂。石柳和八号栾奕,他们都是浑身沾满油腻的普通工人,然而,恰恰是他们,凭借一个独立的个人良知和丰富的人生经验,最早看出了假引资的破绽。栾奕在被麦娜误解时,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石柳在全皓回到这座城市时,毅然揭露了房地产公司表面上是“杜总”执柄,而实际上秘书长是董事长的秘密;还有牛仔布厂的几个姐妹,毕姐的甘贫乐道,曾繁枝的淳厚朴实,娄云追赶时髦到最后的堕落,尹雀的痴迷于“多头恋爱”和“情书写手”……虽然性格爱好各不相同,但她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样热爱牛仔布厂,同样热爱自己的工作,即使当工厂拍卖失业后,他们依然在社会夹缝里苦苦寻找各自的生存空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对于小胡子这个形象的塑造,并且赋予他以复杂的性格。他很狡黠,也很世故。然而,正如席勒所说:“任何人,即使是最坏的人,他们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上帝的影子来”。当全皓和麦娜为推销滞销牛仔布而奔忙时,他慷慨襄助,尽管其手段有违于经济伦理,然而,却也不乏人性的光彩。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些普通的生命,这座城市就会失去骨骼。
这里是道德的审判台,催发善端的复苏和良知的发现。南楠这个人物,仅次于全皓和麦娜,是作家着墨较多的一个人物,也是背着十字架走向天国的悲剧人物。我觉得,梦萌艺术思维的老成正在于没有把他刻画成一个绝对的坏人。从情感上说,他对麦娜的爱情是真实的,也没有错。他错在最终无法走进麦娜的情感深处。在得知麦娜因为“未见红”问题而被全皓冷落,他也不乏男人的责任感,从而酿成宁愿挨宰,也要接受滞销的牛仔布,以及最后为解脱麦娜而杀死秘书长的违法犯罪。这样一个复杂人物,进一步诠释了城市复杂、多元、立体的文化生态。
作品在降下它悲剧的帷幕时,全皓和麦娜面对秘书长和南楠双双被刺的惨烈,争相承担法律责任,要代对方向公安部门自首,以救赎因为彼此伤害而负疚和负罪的灵魂。解脱他们,固然要靠法律的甄别,然而,振作他们,还要靠文化的自觉、自醒。法律不会因为他们戴罪而放弃对南楠和全皓的制裁,他们也不可能从代人顶罪中获得灵魂的安妥,唯一的选择,是通过文化的自省振作起来,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
这是作家留给读者的审美空间。
而城市,就在这样的氤氲下书写着自己的风流;依偎在城市怀抱中的人们,就在这样的光束下,绵延着自己“历时态”的悲欢离合。
(原载新浪、凤凰、网易等各大网站,后被收录于多部文集)


作者简介
杨焕亭,中共党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五届理事,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先后在人民日报等国内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近500万字。出版散文集、学术专著、长篇人物传记、长篇小说计14部。长篇小说《汉武大帝》《武则天》《汉高祖》均为三卷本,计370万字,被学界称为历史题材“三部曲”。其中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获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参评茅盾文学奖评选。作品曾多次在国内评奖中获得奖次。
责任编辑:韩雪
2025-07-15 17:24:46
2025-07-15 09:25:50
2025-07-15 09:16:58
2025-07-14 17:39:44
2025-07-14 14:05:55
2025-07-14 14:04:42
新闻动态
公益明星
榜样人物
草根故事
热门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