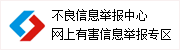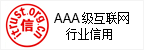父母的爱情
我总以为,爱情属于年轻人,老年人是没有爱情的,他们只有婚姻,只有搭伙居家过日子,特别是农村没文化的老人。我的父母一辈子生活在农村,没什么文化,在我最初的粗浅认知中,他们不会有爱情,也不懂爱情。相爱的人之间,一声名字的唿唤,都会让骨头酥麻。而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听到母亲唿唤过父亲的名字,更多的是眼神相顾对视,然后“唉”一声,就算是打招唿了。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确从未当面叫过父亲的名字。她总是站在门槛上,朝着田埂或是父亲从外面回家的方向远远观望,直到看到父亲的身影,才轻唤一声“唉”,尾音带着些微的上扬,像春日里拂过柳梢的风,轻缓而温柔。那时父亲在公社当干部,早出晚归是常事,有时去县城开会,就要好多天。母亲便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居住在乡下老屋内。母亲在安顿好儿女之后,还得赶时间到生产队里挣工分,从未因“干部家属”的特殊的身份,讨过半点优待。父母虽然没有文化,但他们的婚姻也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年,已经是公社干部的父亲到母亲村里工作,年近而立之年的父亲,不经意间遇到了小他八岁的母亲。当时,父亲家里很穷,穷得只有孤儿寡母相依度日。于是,父亲就开玩笑说,要给母亲说媒,介绍一个好人家。说着说着,父亲却把母亲说给了自己。母亲的娘家也是贫穷人家,当时母亲看父亲老实本分,大小也是个公社干部,也就没要什么彩礼,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嫁妆。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日子,没有三书六聘,也没有八抬大轿,甚至没有办酒席,母亲只是简单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拎着一只非常简易的藤编小箱,就和父亲牵手到公社里登记了。嫁给父亲之后,母亲秉承了农村妇女的勤劳与朴实,做起了贤妻良母,让父亲安心在外工作,由母亲在家收拾家务,照顾年迈的婆婆。已属大龄青年的父亲从此也结束了单身生活。因为母亲的到了,父亲的家也就更像家了。在我童年时期,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母亲也是一刻不得空闲。每天窗外还泛着青灰,母亲就把我从被窝里抱出来,然后放在草筐内,一头挑着垃圾,一头挑着我,下地干活。到了地头,母亲忙着劳动,我则坐在田埂上,与青蛙、蛐蛐为伍,半天时间下来,我通常成了泥猴子,整张脸除了两个眼睛还闪着光亮外,脸上、身上全涂满了泥巴,惹得母亲不得不耗费好一阵子给我收拾干净。到了收工时,母亲又一声不吭地把我放进草筐一头,另一头则装满了刚割来的青草或捡来的柴火,然后弯着嵴背挑着回家。草筐里的我全然感受不到母亲的辛劳,反而会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摇晃,甚至看见她后颈上细密的汗珠,顺着发尾滴在衣领上,在衣服后背晕开深色的花斑。当时,乡下农家是没什么菜的,一年到头都过着“饭在钵里,菜在坛里”的日子,咸菜萝卜条是四季家常。只有父亲偶尔回家时,母亲才会变着花样整两个小菜,或炒点花生米,或煎个鸡蛋,让工作辛苦的父亲能回家感受一点温暖。通常,外面回家的父亲会坐的家门口喝茶,母亲则在灶台前忙上忙下,一会往炉膛里添一把柴草,一会又用锅铲搅动着铁锅。饭菜的香味随蒸汽漫上来,母亲的眼角细纹也变得柔软开来。“唉,好吃饭了。”她朝着门口喊了声,声音里带着些不易察觉的温柔。早已司空见惯的父亲心神领会,便带着一脸幸福走进家门。如果遇到天气特别热的傍晚,母亲就把小桌子搬到门口,然后一家人就着点点星光,围着小桌子共进晚餐。这个时候,承欢在父母膝下的我,是最快乐的时光。有好吃的,母亲都会留给父亲,或是留给子女,自己从来舍不得吃一口。母亲最爱吃的,就是农村菜坛子里腌制的咸菜萝卜条。直到后来家里生活条件好了,母亲还是爱吃咸菜萝卜条,每年家里都要腌制几大坛。吃腌萝卜条时,母亲把萝卜嚼得脆响,嘴角沾着细碎的卤汁。母亲把好吃的留给父亲和儿女之后,她的脸上,也是满眼笑容。
因为工作关系,父亲居家的日子很少,在他要外出的前夜,母亲总要在油灯下坐很久。她翻出父亲唯一的”客衣”,对着灯光细细查看,发现袖口磨开了花,便从抽屉里扯出半块新布,穿针引线缝补上去。布是靛青染的,在月光下泛着幽蓝的光,母亲的手在布面上穿梭,像在缝补一段漫长的时光,也像在缝制她的幸福生活。第二天一早,母亲把打好的包袱放在父亲床头,里面除了换洗衣物,还有用油纸裹着的麦饼——那是她半夜爬起来烙的,面里和了桂花和砂塘,带着淡淡的甜香。父亲把铁皮茶杯塞进包袱,母亲又往里面塞了把油纸伞:“唉,广播里天气预报说有雨,先带上吧。”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就起身了,他的布鞋声在房间里响起,母亲披着衣服站在门口,看着那抹模煳的身影消失在晨雾里,许久才转身,把父亲睡过的草席重新铺平整。父亲回来时,总会带些集市上的稀罕物:一小包红糖,半块肥皂,或是给我们姐弟的一支铅笔。母亲接过东西,嘴上抱怨着“乱花钱”,却满心欢喜地把红糖收进瓦罐,肥皂用剩的碎渣都攒在竹篮里,舍不得丢弃。虽然是脱产干部,但父亲从没真正脱过产。一回到家,就换上一件破旧的衣裳,帮衬着母亲待弄田里的庄稼,一刻也不得空闲。当时,我幼小的心里感觉挺纳闷的:“干农活又累又苦,父亲怎么这样喜欢呢?”也许只有母亲明白父亲的心思:“你爸这是以前饿肚皮饿怕了,过去家里穷,没田没地,自然也就没得吃,饥一顿,饱一顿地对付着,现在分到田地了,身上的劲也有处使了,他当然干得欢了。”父亲退休那年,我刚好初中毕业,到镇里读高中。父亲则穿回以前在农村劳动时穿的蓝布衫,腰间又围着一搭乡下人常用的“汤布”,说:“这下,又能回家当农民了。”正在灶间烧水的母亲,有些恼怒地说道:“唉,别人都挖空心思逃离农田劳动,你怎么这样想回来当农民呢。”父亲蹲在门槛上卷烟叶,指尖沾着金黄的烟末,头也不抬,一边从门后抡起锄头,一边回应道:“种田地,万万年,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还是当农民好,脚踩黄土心里踏实。”从此,父亲又真正成了地道的农民。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出门,晌午也不回家,就往田埂上一坐,从布兜里掏出自带的煮番薯或煮毛芋,就着一大壶凉水,胡乱对付一顿。有一回,我刚从学校回家,就去给父亲送午饭,看见他正赤膊挥着竹鞭在犁田,古铜色的嵴背在烈日下泛着光亮,裤腿卷得老高,脚底板结着厚厚的茧子,倒真像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母亲常说,父亲当了一辈子公社干部,临退休了也没学会当官的派头,倒把农民的本分刻进了骨头里。冷不丁在路上碰到,陌生人绝对想像不到,这个牵着牛在犁田的老农民,曾经还当过公社书记。后来,上完高中的我没考上大学,也一脸沮丧地回家当了农民。这下,父亲不愠不恼,还宽慰我说:“中国有十多亿农民哩,现在有田有地有力气,当农民也是不错的。”在田间劳动时,父亲可比我更像农民,犁耙耕耖,四季农事,样样精通,倒是我像个公子哥,老爱穿着鞋下地,惹得父亲多次对我破口大骂:“干活没个干活的样子,下地劳动又不是机关坐办公室,赤个脚难道还怕蚱蜢咬啊?”做不惯农活的我一边在田里劳动,一边想着怎样脱离苦海。在忍受了父亲对我十三年的唠叨之后,最终我还是逃离了农村,把一家子的田地都留给了父亲。田里少了我这个帮手,父亲就更忙碌了。农忙时,母亲也跟着父亲下田。她的手因为常年握针线,早已磨出了硬茧,却仍能熟练地插秧、割稻。父亲在前头犁地,牛蹄踩过湿润的泥土,翻出黑色的沃土,母亲跟在后面,把漏下的草根一一捡起。日头偏西时,父亲直起腰,捶捶发酸的嵴背,母亲便递上竹筒水:“唉,歇会儿吧。”两人坐在田埂上,看远处的炊烟袅袅升起,像一条白色的丝带,系着人间的烟火。年事渐高的父亲惭惭做不了农活了,母亲便接过父亲手中的锄头,自己下地干活,不允许父亲去干重活了。可是,父亲闲不住,总是忘不了到田头地角去,种些时令蔬菜。母亲见劝不住父亲,便会说:“唉,你也就是个劳碌命,一辈子离不开锄头,离不开田地。”声音里带着心疼,生怕惊飞了一只受伤的鸟。逃离农村之后,我最终还是把家里的土地流转出去了。没有田地的父亲再也不用每天想着到田里去劳作了。闲不住的父亲就迷上了中医针炙,他买了中医针炙书籍,备齐了一整套针炙设备,然后在自己的腿上、手臂上找穴位,练习扎针。慢慢的,父亲掌握了针炙原理后,就会骑着自行车,去邻村转转,张罗着为一些患有腰痛病、坐骨神经痛的村民免费扎针。也有一些村民在扎了针炙之后,感觉疼痛减缓了,这时,父亲就会开心得像个小孩。看着父亲整天忙碌的身影,母亲默默承受着一个家的责任,对于不着家的父亲,母亲没有半点埋怨:“唉,他喜欢就让他做吧,难得现在不下地干活了。”
一个春节之后的傍晚,父亲从邻村回家途中,骑车途经一座坦水桥时,不慎摔落桥下,此时路边空无一人,父亲就这样突遭飞天横祸,永远离世了。对于父亲的突遭不恻,母亲顿觉天旋地转,她万万也没有想到,为人处事正直、善良的父亲,怎么会遇此大难?难到真的应验了那句俗话:“好人不留种,阎王收着走。”母亲虽然不信鬼神,她一直认为,人死之后,就会化为泥土,与大地融为一体。但在父亲的葬礼中,她坚持要按一坟双穴的规格,把自己的墓穴也修筑在父亲墓旁,这样,母亲百年之后,可以追随父亲,在另一个世界再续前缘。父亲刚走的日子里,母亲极度不适应这样孤独的日子,陪伴她的只是父亲冰冷的遗像。母亲只能把父亲的遗像擦了又擦,然后摆在床头柜上,就像父亲依然静静地陪伴着母亲。往后的二十多年,母亲的日子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她每天清晨都会坐在院子里择菜,择着择着就发起呆来。阳光穿过院子里的枇杷树,在她银白的头发上撒下细碎的光斑,母亲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和墙上父亲的影子叠在一起,像是从未分开过。父亲离世后,原本话语不多的母亲就更加沉默了。更多的时候,母亲都是一个人静静地站在父亲的遗像前,含悲落泪,虽然没有哭出声音,但布满皱纹的老脸上,早已泪水模煳。这种亲人离去之后的无奈与悲凉,深深地刺痛了我内心的神经,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血肉相连。好几次我从外面回家,母亲都是流着泪,在父亲的遗像前站立,让儿女看到心疼不己,只能好言相劝着把母亲搀扶到房间内,这种场景直到我造了新楼房,把母亲从老房子里搬出才结束。搬到新房子里后,母亲早早地把父亲的遗像带到身边,在她的房间里正中摆放。父亲遗像的相框用金色花边镶嵌,时间久了,边缘的漆色早已斑驳,母亲就用旧软布细心擦拭,直到她在竹椅上睡去,玻璃上还留着一道斜斜的指纹印,像是时光拓下的一枚印章。后来,母亲又早早地把自己的相片拍好,放大之后,如同父亲的遗像规格,做了边框,摆放在抽屉里,然后盯瞩儿女,在她百年之后,要和父亲的相框摆放在一起。不识字的母亲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子女,父母之间的感情早已根深蒂固,不容分割,已达到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境界。将近50年光阴的朝夕相处,他们之间虽然没有举案齐眉、红袖添香的浪漫,但彼此已经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母亲去世后,我遵循她的遗愿,将母亲的骨灰安放在原先顶制好的墓穴中,她终于又陪伴在父亲身边了。如果真的有另一个世界,我想,此时的母亲,一定已经与父亲重新相逢,她每天用粗糙的双手,给父亲整理待穿的衣物,给父亲准备远行的烙饼,用她一声声“唉”的唿唤,连接与父亲的情感纽带。我这才恍然,父母之间并非没有爱情,他们也是有爱情的,只是他们的爱情太过安静,像地下的静静流淌的暗河,不为人所见,却从未停止过涌动。他们的爱情不在言语中,不在拥抱里,而在母亲为父亲补过无数次的衣领上,在父亲为母亲捎回的那块花布里,在母亲站在遗像前无声的泪水内,在父母百年之后一墓双穴的生死相依中。他们的爱情不是花前月下,不是卿卿我我,不是你侬我侬,而是普普通通的烟火日常。日复一日的厮守,阴阳相隔的思念。父母的爱情,就像他们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朴实无华,孕育了生命,也滋养了岁月。 作者简介:戴建东,男,浙江金华人,1965年8月出生,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散文学会会员。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曾从事石匠、泥瓦匠、代课教师、新闻记者等职业,在中央、省、市报刊发表作品100多万字,后通过自学获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现供职政府机关新闻中心。曾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诗合集《九峰派诗选》、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散文集《行走田园》、文汇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星星落进了小河》。
作者简介:戴建东,男,浙江金华人,1965年8月出生,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散文学会会员。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曾从事石匠、泥瓦匠、代课教师、新闻记者等职业,在中央、省、市报刊发表作品100多万字,后通过自学获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现供职政府机关新闻中心。曾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诗合集《九峰派诗选》、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散文集《行走田园》、文汇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星星落进了小河》。
因为工作关系,父亲居家的日子很少,在他要外出的前夜,母亲总要在油灯下坐很久。她翻出父亲唯一的”客衣”,对着灯光细细查看,发现袖口磨开了花,便从抽屉里扯出半块新布,穿针引线缝补上去。布是靛青染的,在月光下泛着幽蓝的光,母亲的手在布面上穿梭,像在缝补一段漫长的时光,也像在缝制她的幸福生活。第二天一早,母亲把打好的包袱放在父亲床头,里面除了换洗衣物,还有用油纸裹着的麦饼——那是她半夜爬起来烙的,面里和了桂花和砂塘,带着淡淡的甜香。父亲把铁皮茶杯塞进包袱,母亲又往里面塞了把油纸伞:“唉,广播里天气预报说有雨,先带上吧。”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就起身了,他的布鞋声在房间里响起,母亲披着衣服站在门口,看着那抹模煳的身影消失在晨雾里,许久才转身,把父亲睡过的草席重新铺平整。父亲回来时,总会带些集市上的稀罕物:一小包红糖,半块肥皂,或是给我们姐弟的一支铅笔。母亲接过东西,嘴上抱怨着“乱花钱”,却满心欢喜地把红糖收进瓦罐,肥皂用剩的碎渣都攒在竹篮里,舍不得丢弃。虽然是脱产干部,但父亲从没真正脱过产。一回到家,就换上一件破旧的衣裳,帮衬着母亲待弄田里的庄稼,一刻也不得空闲。当时,我幼小的心里感觉挺纳闷的:“干农活又累又苦,父亲怎么这样喜欢呢?”也许只有母亲明白父亲的心思:“你爸这是以前饿肚皮饿怕了,过去家里穷,没田没地,自然也就没得吃,饥一顿,饱一顿地对付着,现在分到田地了,身上的劲也有处使了,他当然干得欢了。”父亲退休那年,我刚好初中毕业,到镇里读高中。父亲则穿回以前在农村劳动时穿的蓝布衫,腰间又围着一搭乡下人常用的“汤布”,说:“这下,又能回家当农民了。”正在灶间烧水的母亲,有些恼怒地说道:“唉,别人都挖空心思逃离农田劳动,你怎么这样想回来当农民呢。”父亲蹲在门槛上卷烟叶,指尖沾着金黄的烟末,头也不抬,一边从门后抡起锄头,一边回应道:“种田地,万万年,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还是当农民好,脚踩黄土心里踏实。”从此,父亲又真正成了地道的农民。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出门,晌午也不回家,就往田埂上一坐,从布兜里掏出自带的煮番薯或煮毛芋,就着一大壶凉水,胡乱对付一顿。有一回,我刚从学校回家,就去给父亲送午饭,看见他正赤膊挥着竹鞭在犁田,古铜色的嵴背在烈日下泛着光亮,裤腿卷得老高,脚底板结着厚厚的茧子,倒真像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母亲常说,父亲当了一辈子公社干部,临退休了也没学会当官的派头,倒把农民的本分刻进了骨头里。冷不丁在路上碰到,陌生人绝对想像不到,这个牵着牛在犁田的老农民,曾经还当过公社书记。后来,上完高中的我没考上大学,也一脸沮丧地回家当了农民。这下,父亲不愠不恼,还宽慰我说:“中国有十多亿农民哩,现在有田有地有力气,当农民也是不错的。”在田间劳动时,父亲可比我更像农民,犁耙耕耖,四季农事,样样精通,倒是我像个公子哥,老爱穿着鞋下地,惹得父亲多次对我破口大骂:“干活没个干活的样子,下地劳动又不是机关坐办公室,赤个脚难道还怕蚱蜢咬啊?”做不惯农活的我一边在田里劳动,一边想着怎样脱离苦海。在忍受了父亲对我十三年的唠叨之后,最终我还是逃离了农村,把一家子的田地都留给了父亲。田里少了我这个帮手,父亲就更忙碌了。农忙时,母亲也跟着父亲下田。她的手因为常年握针线,早已磨出了硬茧,却仍能熟练地插秧、割稻。父亲在前头犁地,牛蹄踩过湿润的泥土,翻出黑色的沃土,母亲跟在后面,把漏下的草根一一捡起。日头偏西时,父亲直起腰,捶捶发酸的嵴背,母亲便递上竹筒水:“唉,歇会儿吧。”两人坐在田埂上,看远处的炊烟袅袅升起,像一条白色的丝带,系着人间的烟火。年事渐高的父亲惭惭做不了农活了,母亲便接过父亲手中的锄头,自己下地干活,不允许父亲去干重活了。可是,父亲闲不住,总是忘不了到田头地角去,种些时令蔬菜。母亲见劝不住父亲,便会说:“唉,你也就是个劳碌命,一辈子离不开锄头,离不开田地。”声音里带着心疼,生怕惊飞了一只受伤的鸟。逃离农村之后,我最终还是把家里的土地流转出去了。没有田地的父亲再也不用每天想着到田里去劳作了。闲不住的父亲就迷上了中医针炙,他买了中医针炙书籍,备齐了一整套针炙设备,然后在自己的腿上、手臂上找穴位,练习扎针。慢慢的,父亲掌握了针炙原理后,就会骑着自行车,去邻村转转,张罗着为一些患有腰痛病、坐骨神经痛的村民免费扎针。也有一些村民在扎了针炙之后,感觉疼痛减缓了,这时,父亲就会开心得像个小孩。看着父亲整天忙碌的身影,母亲默默承受着一个家的责任,对于不着家的父亲,母亲没有半点埋怨:“唉,他喜欢就让他做吧,难得现在不下地干活了。”
一个春节之后的傍晚,父亲从邻村回家途中,骑车途经一座坦水桥时,不慎摔落桥下,此时路边空无一人,父亲就这样突遭飞天横祸,永远离世了。对于父亲的突遭不恻,母亲顿觉天旋地转,她万万也没有想到,为人处事正直、善良的父亲,怎么会遇此大难?难到真的应验了那句俗话:“好人不留种,阎王收着走。”母亲虽然不信鬼神,她一直认为,人死之后,就会化为泥土,与大地融为一体。但在父亲的葬礼中,她坚持要按一坟双穴的规格,把自己的墓穴也修筑在父亲墓旁,这样,母亲百年之后,可以追随父亲,在另一个世界再续前缘。父亲刚走的日子里,母亲极度不适应这样孤独的日子,陪伴她的只是父亲冰冷的遗像。母亲只能把父亲的遗像擦了又擦,然后摆在床头柜上,就像父亲依然静静地陪伴着母亲。往后的二十多年,母亲的日子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她每天清晨都会坐在院子里择菜,择着择着就发起呆来。阳光穿过院子里的枇杷树,在她银白的头发上撒下细碎的光斑,母亲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和墙上父亲的影子叠在一起,像是从未分开过。父亲离世后,原本话语不多的母亲就更加沉默了。更多的时候,母亲都是一个人静静地站在父亲的遗像前,含悲落泪,虽然没有哭出声音,但布满皱纹的老脸上,早已泪水模煳。这种亲人离去之后的无奈与悲凉,深深地刺痛了我内心的神经,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血肉相连。好几次我从外面回家,母亲都是流着泪,在父亲的遗像前站立,让儿女看到心疼不己,只能好言相劝着把母亲搀扶到房间内,这种场景直到我造了新楼房,把母亲从老房子里搬出才结束。搬到新房子里后,母亲早早地把父亲的遗像带到身边,在她的房间里正中摆放。父亲遗像的相框用金色花边镶嵌,时间久了,边缘的漆色早已斑驳,母亲就用旧软布细心擦拭,直到她在竹椅上睡去,玻璃上还留着一道斜斜的指纹印,像是时光拓下的一枚印章。后来,母亲又早早地把自己的相片拍好,放大之后,如同父亲的遗像规格,做了边框,摆放在抽屉里,然后盯瞩儿女,在她百年之后,要和父亲的相框摆放在一起。不识字的母亲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子女,父母之间的感情早已根深蒂固,不容分割,已达到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境界。将近50年光阴的朝夕相处,他们之间虽然没有举案齐眉、红袖添香的浪漫,但彼此已经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母亲去世后,我遵循她的遗愿,将母亲的骨灰安放在原先顶制好的墓穴中,她终于又陪伴在父亲身边了。如果真的有另一个世界,我想,此时的母亲,一定已经与父亲重新相逢,她每天用粗糙的双手,给父亲整理待穿的衣物,给父亲准备远行的烙饼,用她一声声“唉”的唿唤,连接与父亲的情感纽带。我这才恍然,父母之间并非没有爱情,他们也是有爱情的,只是他们的爱情太过安静,像地下的静静流淌的暗河,不为人所见,却从未停止过涌动。他们的爱情不在言语中,不在拥抱里,而在母亲为父亲补过无数次的衣领上,在父亲为母亲捎回的那块花布里,在母亲站在遗像前无声的泪水内,在父母百年之后一墓双穴的生死相依中。他们的爱情不是花前月下,不是卿卿我我,不是你侬我侬,而是普普通通的烟火日常。日复一日的厮守,阴阳相隔的思念。父母的爱情,就像他们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朴实无华,孕育了生命,也滋养了岁月。

责任编辑:
相关阅读
2003年6月的一个下午,我们突然接到江总书记的指示,要求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负责接待从美国归来的孙中山先生孙女——孙穗芳女士。接到命令后,我们立刻紧锣密鼓地筹
2025-06-16 09:34:27
2010 年盛夏,当我以新闻系毕业生的青涩姿态踏入报社时,命运的齿轮已然转动。那年偶然邂逅的姻缘,不仅让我与爱人携手伴侣,更让我有幸走近了活跃在陕西文坛的作家梦萌先生。这位
2025-06-15 21:07:17
西北建设杂志社 古城西安,华灯绽放。参加完朋友们盛宴后返回宾馆,惊喜收到好友杨居平先生刊发在今日头条:安康人周末读书会,共读《恒河源一一叶坪记忆》,感受家乡文化魅力阅
2025-06-14 21:46:09
西北建设杂志社 岭南是中国荔枝的盛产地,来到“荔枝之乡”广东增城,有幸能在芒种前一天尝到第一批成熟佳果“妃子笑”,这就要十分感谢赠果主人雷永江
2025-06-13 22:15:23
编者按:在地理与艺术的交汇处,金京模先生的《地貌类型图说》系列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地球表面的窗口。这组作品不仅展现了画家精湛的技艺,更通过艺术化
2025-06-13 22:14:01
西北建设杂志社 在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由未央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指导,大明宫街道办、区文化馆、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主办的“融入现代生活•非遗正
2025-06-13 22:02:22
新闻动态
公益明星
榜样人物
草根故事
热门标签